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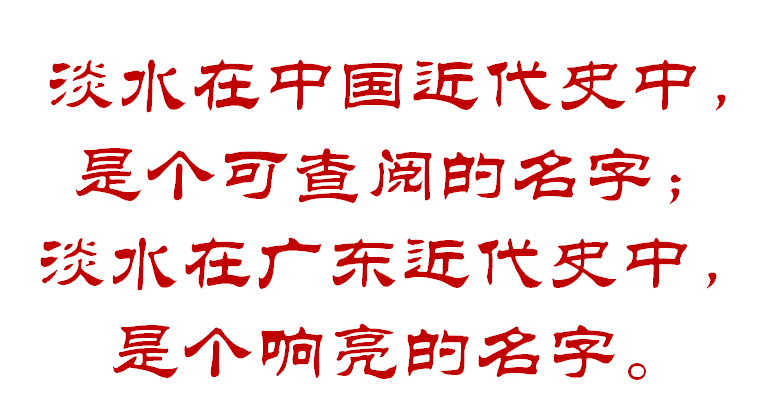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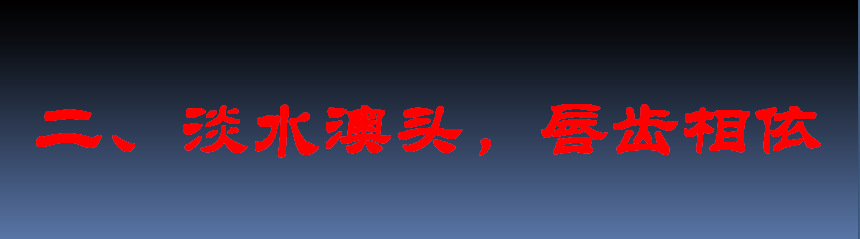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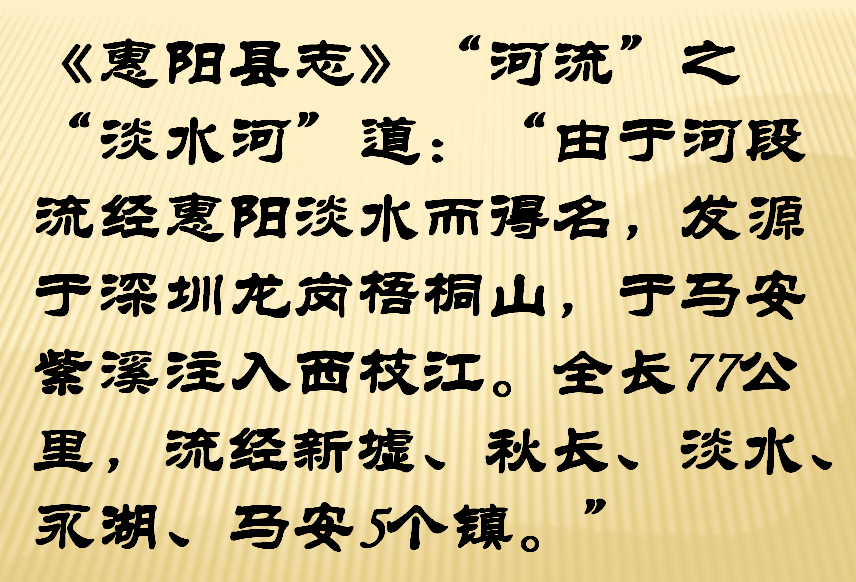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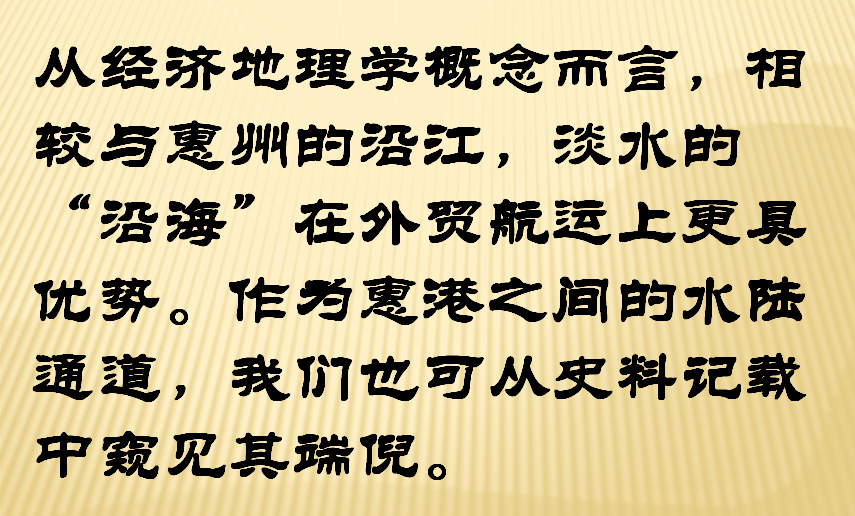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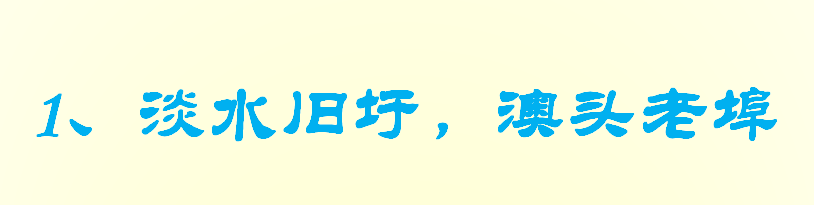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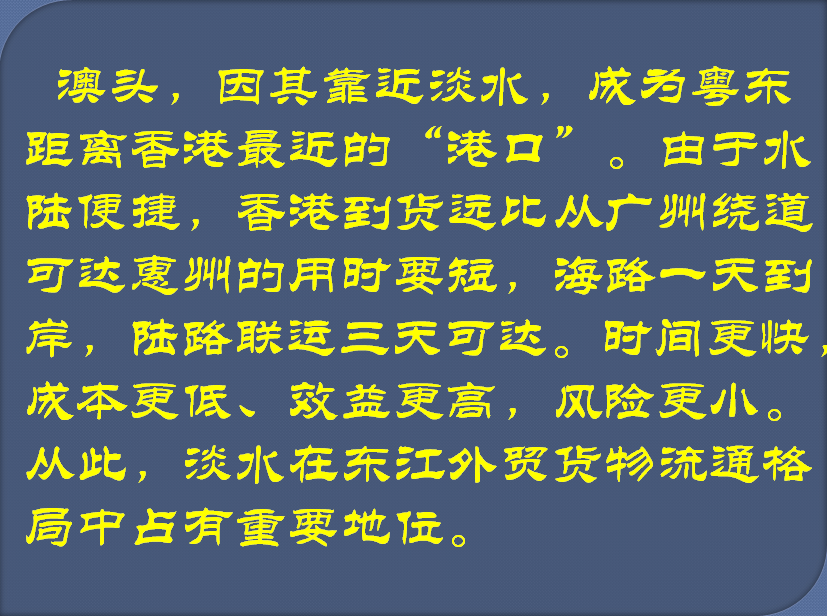
《惠阳县志》“河流”之“淡水河”道:“由于河段流经惠阳淡水而得名,发源于深圳龙岗梧桐山,于马安紫溪注入西枝江。全长77公里,流经新墟、秋长、淡水、永湖、马安5个镇。”从经济地理学概念而言,相较与惠州的沿江,淡水的“沿海”在外贸航运上更具优势。作为惠港之间的水陆通道,我们也可从史料记载中窥见其端倪。
澳头,因其靠近淡水,成为粤东距离香港最近的“港口”。由于水陆便捷,香港到货远比从广州绕道可达惠州的用时要短,海路一天到岸,陆路联运三天可达。时间更快,成本更低、效益更高,风险更小。从此,淡水在东江外贸货物流通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。
叶地编《广东地名探源》云“淡水镇”:位于惠阳县南部。考惠阳淡水一名,始于宋,元丰《九域志》载之淡水盐场,非今淡水镇也,而在今惠东县之平海。明清又置淡水场,才在今地。民国时又作澹水圩。据调查,原为上圩、锅笃圩,二圩并为一,称淡水,因淡水河经过得名。
清咸丰初年,淡水詹、戴、李三姓民众为防械斗,修筑淡水古城墙。据杨振林作《淡水古城墙》介绍:“古城墙全长约3150米、高3米、厚0.6米。建有东门、烧炮台门(今南门)、猪行门(今镇一小新校门)、河坝下城门(今北门)、坝尾城门(今西门)、木莲桥城门(今镇二小左侧),另设三个便门。城门高度均为2.5米、宽度均为1.5米,四框均用花岗岩石建造。烧炮台门为淡水古城交通要道之一,可通大亚湾畔的澳头、霞涌两镇出海往香港;河坝下城门到淡水河挑水(当时淡水河清澈无污染)、洗衣服。亦是县内河运之咽喉,到建国前,商务颇为繁忙。”
2018年第1期《惠州故事》中的《惠州城址变迁》一文,“淡水古城”部分介绍:“清乾隆初期,淡水形成了较大的集镇,并改名为‘淡水墟’,设立‘司署’和盐大使,墟市设在上下淮(今淡水桥头市场一带)。”
淡水商业可追叙的史料,又见《惠城文史资料》第十三辑,由惠州市博物馆原馆长王宏宇所作《清代乾隆年间的惠州商会行业》。文中讲道:“桥东包公巷内的包公庙保存有两通石碑,一通为乾隆十九年(1754)的‘重修孝肃包公庙碑记”。该碑“店铺录述”中,便例有“淡水木厂”。按此推理,木厂这类民生作坊都有“配套”,当时淡水圩常住人口规模应在万人上下。而“淡水木厂”,身世又存在二种可能:其一是商家因便利,自行命名,与淡水圩没有关联;其二是它是来自淡水圩商家,又在归善县城开设木厂分号。就《惠州城址变迁》中“淡水墟”的行政功能和管辖配置而言,我们倾向于“其二”这一答案。
《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》云:“香港设埠。广东百货皆聚于斯。洋商遂亦乐居其地。西人之在中国者。近年统计不及七千人。而香港则居十之六焉。”香港与内地的来往更加密切频繁,其中商业的因素最为主要。《淡水今昔》中:“再说澳头。最早的港口是在渡头河上游,妈庙区西门村西北,向称盐步头港(又称盐埠头)。早在明朝时已有船航行沿海各地。鸦片战争后,香港成市,由澳头出港的人逐年增多。廿年代有小火轮名‘德星’号由澳头直通香港,每天早晚往返一次。”
淡水旧时虽是“依河而生,渔盐而兴”的圩镇。但随着鸦片战争中中国的惨败,西方列强的黑手开始伸向各个沿海口岸,而淡水的核心优势在于,它具有与海洋运输业接驳成为“口岸”的先天条件,澳头的作用仅仅是“到岸”。纠其原因,澳头尚不具备的口岸功能淡水皆有。如:仓储完善和交通便利等配套服务设施,它可极大地节约时间,提高效率,为商家节省大量成本。
由于特殊时代造成的特殊原因,我们不得不又将话题转到鸦片上来。实际上,淡水的“开埠”紧随香港城市基建与贸易开始。当时正处于前后共计三十年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,鸦片本身,就是当时香港输出的主要“贸易商品”。中国东南沿海鸦片战争后兴起的城市,如汕头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等地,其中包括淡水,无不首当其充,概莫能免。
自1858年签订的《天津条约》中,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化。鸦片改头换面成了“洋药”,从而毒害中国人民,将中华民族推入危亡边缘。法包利威著《中国鸦片史》中“鸦片及资本主义的发展”讲到:“首先应该承认,鸦片贸易的确为财富的集中提供了便利条件。从19世纪30年代起买办们暴敛大量财富,然后再拿这笔钱向英商购买鸦片。我们在前文也提起过一些短时间内暴富的鸦片商人,提起过粤商行会早期对北方市场的控制,鸦片贸易也因此集中控制在少数人手里。”罪恶的“鸦片贸易”,是乎成为当时敛财暴富的唯一模式。
英国人的可耻与中国人的可悲,都是那个时代的面孔特写。
无需承担走私的风险,即同样能够获得高额的利润回报,试想,鸦片经销“窑口”在何处不兴旺?早期淡水商户所经历资本的原始积累,是否能够绕开鸦片经销这一“罪恶”,已不是值得探究的问题。
当时的洋货买卖之中,以鸦片为主,却不是唯一。清番禺陈灃作《炮子谣》唱道:“通商皆由好洋货,钟表绒羽争辉煌。”当然,这类花俏的商品,也只能在较大的“口岸”销售。
《近代粤商与社会经济》中“南北行和金山庄”有载:“南北行是香港商业发轫期最重要的行业之一,中国内地土特产和南洋货品,都经由其进行转口贸易。该行的商家长期控制香港的米行、药材行、瓷器行、纸业、茶叶行、凉果行、柴碳业、汇兑及侨批等业。”《惠州城址变迁》中“淡水古城”介绍:“咸丰初年,形成猪行街、大鱼街、米街、灯笼街等商品交换专业街道,城四周筑有城墙,长3150米,设东门、烧炮台门、猪行门、河坝下门、木莲桥门。”
鸦片及洋货泛滥内地,只因淡水与香港交通便利。洋货运输成本低、利润高、周转周期快等因素,使淡澳买办商人获利颇丰。而一旦货物进入淡水,不用兜兜转转,则可由此进入粤东北内陆各县,东江流域的惠州、平山(今惠东)、博罗、河源、老隆、兴宁乃至梅州而暢通无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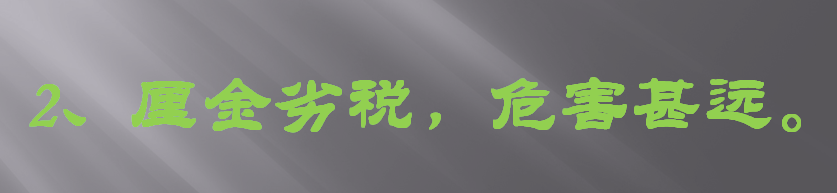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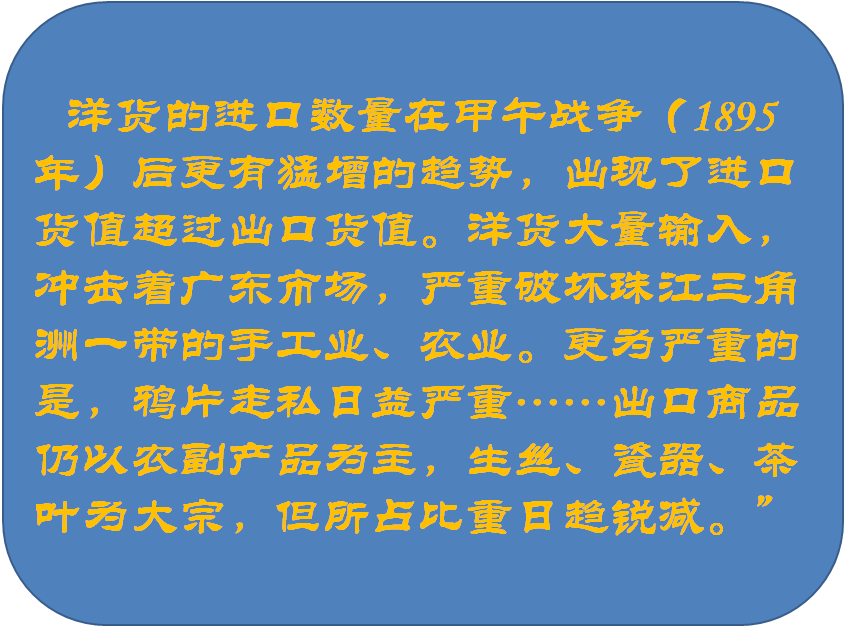
据《广东省志·对外经济贸易志》之“明清时期的对外经济贸易(之二)”部分介绍:“战后,广东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,洋货的输入除原有的棉、毛织制品外,又增加了火油、钢材、水泥、纸张、机器、染料等,甚至有洋针、洋钉、洋米、洋面粉、洋碱等杂物。这些洋货的进口数量在甲午战争(1895年)后更有猛增的趋势,出现了进口货值超过出口货值。洋货大量输入,冲击着广东市场,严重破坏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手工业、农业。更为严重的是,鸦片走私日益严重……出口商品仍以农副产品为主,生丝、瓷器、茶叶为大宗,但所占比重日趋锐减。”
王孝通著《中国商业史》之“清之商业”中列有“厘金病商”谓:“厘金之害。仅及本国商人,而外商则不受之。即使受害,亦比较甚轻,因外商在中国关税制上,所受种种之优待,本国商人不能同样享受……观此,子口税系优待外商,而厘金则专害华商,数十年来商旅重困,百业凋零,厘金实为最大原因。”
《惠城文史》第三十一辑,所载陈春群著《白沙堆拾遗》一文,“二、白沙厘厂”道:“同治元年(1862)在广州成立省厘务总局,惠州府及所属州县,陆续设厘金局、厂、卡,全面开征厘金。”被称为“恶税之首”的厘金,“逢关收费,遇卡抽厘”已成清同治年来地方获取财税的业态。
据称,厘金制仿自林则徐被遣新疆伊犁屯田时,所倡行劝捐的“一文愿”法。为筹措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军饷,它在早期实行过程中,依然能够保持“关有征而市无征”的制度。但厘金之害又因朝廷竟开放“烟禁”,此举无易于饮鸠止渴。厘金制是特许开通收取鸦片、土特产、百货、花税等税种的通称。
清朝晚期,政府开征厘金加重税收。厘金的征收又分货运的“行厘”与经销的“坐厘”二种。因纳税范围存在的偏差和矛盾,势必造成征收过程的利益冲突。这一时期,朝廷治理弱化,地方势力抬头,各种利益团体的“自治”状况成为潮流。工商业行会便是如此。各地工商业行会具有较强的帮会色彩,故又简称“行帮”。本行各有“堂”号,各行商人推举“值理”,处理和协调本行内部事务,通融权贵,制定规则,强化等级,维护行业垄断。各行会在包征或代替政府收税的同时,也要考虑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得失。由此越来越多地卷入影响地方财政的税收事务当中。
清末《申报》议论:“厘卡之多。犹不止倍于税关之数,其司事巡丁之可畏,亦不止倍于税关之吏役。”清末官声竟有言道:“署一年州县缺,不及当一年厘局差。”
清朝末期田赋、洋关税、盐税、厘金和鸦片税,在淡水一样不少。但早期的淡水,买办洋货暢行无阻,因为有了远避厘金征缴的“保护伞”,成为其较本地商品更多赚取丰厚利润的因素与资本积累的发端。
在金融业务上,西方资本也在不遗余力地打压华商利益。清郑观应《盛世危言》卷四“银行”曰:“若今之洋商所用之银票。并不由中外官吏验看虚实。不论多少。惟所欲为。闻英商汇丰银票在粤通行之票百余万。该行已获利二百余万之谱。虽有华商股份。不与华商往来。”道光二十三年(1843)或稍后,英国在香港设立西印银行,道光二十五(1845)年改名为东方银行。英国政府且授权该行在中国发行钞票(在香港称为东藩汇理银行)。从司法到金融,从贸易到宗教,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,将香港打造成他们殖民远东,奴役中国的支点和基地,一点点蚕食,一步步渗透,将华夏河山支解和吸食得千疮百孔奄奄一息,由半殖民地已乎沦为殖民地的边沿。
更有甚者,港英当局还直接干涉中国金融主权。1887年2月,粤督张之洞奏请清廷创办广东钱局,从技术到设备全部依赖英国。1890年初,铸一元、半元、贰毫、一毫、五分五种“光绪通宝”机制银币。1908年,英国政府借口广东铸造小银币数量太多,影响香港商务,竟提出“限广东每铸大元四万两,搭铸小元八千两”的无理要求。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中国,只能任由列强宰割。
约于此时的50年后,陈炯明运用掌握的权利,对求学所获商业知识及在淡水等地观察到的厘金弊端决定铲除。1911年12月13日,《申报》刋载《陈副督宣布治粤政纲》有云:“第三条。裁去厘金。须定期限。疑将长堤或盐饷为借英款五百万改行抵押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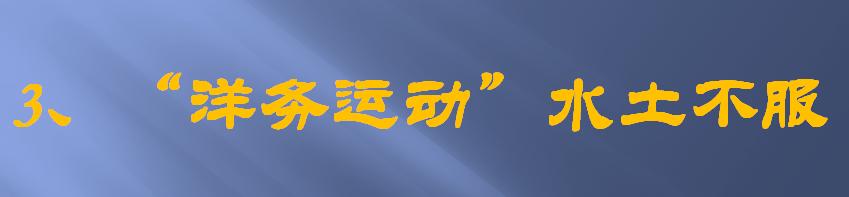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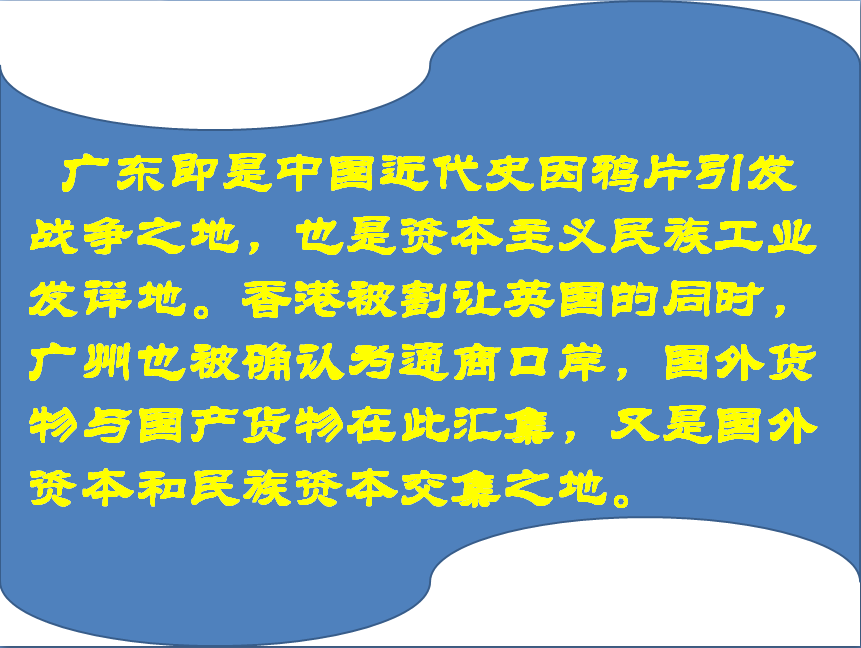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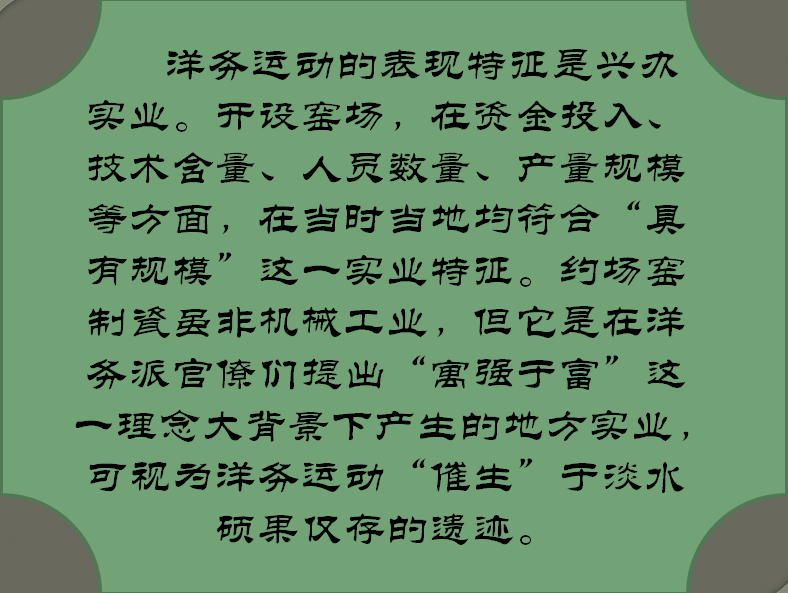
广东即是中国近代史因鸦片引发战争之地,也是资本主义民族工业发详地。香港被割让英国的同时,广州也被确认为通商口岸,国外货物与国产货物在此汇集,又是国外资本和民族资本交集之地。
清同治十三年(1874),李鸿章著《李文忠公奏稿》谓:“东南海疆万余里。各国通商传教。来往自如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。阳托和好之名。阴怀吞噬之计。一国生事。诸国构煽。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。轮船电报之速。瞬息千里。军器机事之精。工力百倍。炮弹所到。无坚不摧。水陆关隘。不足限制。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。”其中对中国落后于西方,以及对未来的担忧表露无遗。
危机意识不仅在朝廷中枢有所增强,社会各阶层更是深受其害者。清刘桢麟《论各省善堂宜设工艺厂以养贫民》有曰:“中国自通商以来。洋货日销。土货日绌。洋纱洋布。岁销五千三百万。其余钟表、机器、呢绒、毡毯、火油、食物、以至纽扣针线之细。皆规我情形。探我玩好。务夺我小工小贩。一手一足之业者。而乃销流日广。始于商埠。蔓于内地。流于边鄙……吾粤如是。余省可知矣。”因此,以容闳、郑观应为首的早期维新人物,提出“富强救国”的维新思想。
工商皆本、经世致用。李鸿章在“中国积弱,由于患贫”的意识下,开启晚清商业、实业“官督商办”的洋务运动。最终变质为“盈亏全归商认,与官无涉。”使“官督商办”落得个有名无实的“幌子”。
惠州是著名侨乡,有“海内一个惠州,海外一个惠州”之称。据统计,现约有300万惠州籍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。在千千万万离乡背井的客家赤子中,叶亚来是最富传奇的代表人物。清道光十七年(1837),叶亚来诞生于淡水沙坑乡周田村。咸丰四年(1854),17岁的叶亚来随乡亲由澳头乘小船往香港,再乘大桅杆船至马六甲,经族叔叶国驷带到榴连冬加的锡矿做工。这位传奇人物36岁被称为“吉隆坡王”。吉隆坡的原意为“泥泞的河口”,经叶亚来率领当地“惠州十邑”华人二十年艰辛打拚,并经营锡矿获得财富。1879年,一跃成为吉隆坡首富。从此,吉隆坡便有“客人开埠”之誉。1883年,清政府授予叶亚来“例授中宪大夫叶茂兰敕赠三代”的荣誉头衔。1884年,47岁的叶亚来汇巨款回淡水,让堂兄弟在周田村购置土地,负责兴建故宅碧滟楼。并计划修建好故宅后回国返乡探亲。时隔一年后,这位华人领袖终因患病去逝,年仅48岁。叶亚来对吉隆坡的贡献,被一代又一代当地华人所铭记,在吉隆坡闹市中的仙四爷庙里,至今供奉叶亚来像。如今淡水尚存的一些城堡式围楼,就是清末南洋归来的华侨所建,其中碧滟楼、会龙楼最具代表性。碧滟楼前的一尊旗杆夹上,仍见刻有铭款:“例授中宪大夫叶茂兰敕赠三代。光绪玖年仲秋月吉日立”字样。
清末上谕:“商民出洋回华。积有余资。自应加意体恤。令其乐归故土。岂容任意苛罚。致令失望。”按照常理,经营有方,归乡心切的叶亚来及其同乡。对在家乡兴办实业,应该有所作为。在对家乡兴建故宅的规模中,“侨资”实力彰显已属贡献较大。林修《淡水今昔》一文介绍:“淡水是著名侨乡。淡澳区总人口十一万九千人,有华侨、港澳台同胞近二十万。但因未查找到确凿史料,在此暂不表述。
太平天国洪仁玗在《资政新编》中,提出“兴器皿技艺”、“兴车马之利”、“兴舟楫之利”、“因时制宜。审时而行”的改良观念。在西方坚船利炮带来的“文明”面前,“洋务运动”成为自我救赎的稻草。
光绪十八年(1893),郑观应刋印《盛世危言》,提出“商战”策略:“凡通商口岸,内省腹地,其应兴铁路、轮舟、开矿、种植、纺织、制造之处,一体准民间开设,无所禁止,或集股,或自办,悉听其便,令以商贾之道行之,绝不拘官场体统。”
据《广东省志·对外经济贸易志》“第一章建国前广东对外经济贸易”内容介绍:“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用大炮轰开广东大门之后,也开始对广东进行掠夺性经济侵略,在不断加大对华商品输出的同时,加强对中国生产原材料的搜刮。为抵御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,广东的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也相继创办一批近代企业。1872年华侨陈启沅在南海创办中国第一家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企业——继昌隆机器缫丝厂;1879年,肇庆旅日华侨卫省轩在佛山创办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火柴厂之一——佛山巧明火柴厂。”
放开禁锢民族工业的枷锁,在这一方面,淡水新墟约场瓷窑这类企业即属“先行先试”,较有成效的民营作坊。
1860年,第二次鸦片战争后,汕头港开埠通商。素有“陶冶之所”称谓的潮州陶瓷生产与出口数量迅速增加,成为对外输出的重要商品。主要外销目的地:一是香港澳门,二是南洋诸国。在商机乍现的世道中,约场瓷窑应市而生。《惠阳县志》“建国前经济”云:“惠阳县历史上较有名的传统工业有纺织、陶瓷、冶铸、藤竹制品、采盐、造船业等。”“隋唐时期,惠阳县已有陶瓷制品生产,到了宋代,陶瓷生产已初具规模。清朝光绪二年(1876),在新圩约场开办了一家官营窑。”遗憾的是,我们始终未能查询到约场窑具有官办性质,并于1876年成立的原始凭据。
今年5月,惠阳博物馆陶振超、惠东政协特邀文史研究员钟土清、南宝东江流域古陶瓷博物馆馆长张旋等,曾率队前往新墟约场,对这座清末古窑址进行实地考察。我们总算是见识到了,在想象中被推断为纯粹以外销为主的,这座生产青花瓷的近代窑口。
洋务运动的表现特征是兴办实业。开设窑场,在资金投入、技术含量、人员数量、产量规模等方面,在当时当地均符合“具有规模”这一实业特征。约场窑制瓷虽非机械工业,但它是在洋务派官僚们提出“寓强于富”这一理念大背景下产生的地方实业,可视为洋务运动“催生”于淡水硕果仅存的遗迹。约场窑随后在宕荡起伏的市场大潮中生存百年,不得不令我们赞叹这家“百年老店”的顽强求生能力。民国年间,陈士光所著《惠阳县调查报告》“建设”部分有:“土碗厂十二窑,工人约百二十余人,出品总值约三万。”其中应包含约场窑当年的数据。
淡水成为惠州府近代手工业发展较快,“工业化”程度较高的圩镇这一事实并非浪得虚名。虽史料不足,但我们断想淡水开设糖厂、织布厂等“实业”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。
被誉为晚清中兴四大臣之一的张之洞,是洋务运动后期代表人物。1886年,他在任两广总督时倡导新学,并创办广雅书局和广雅学堂。光绪十五年(1889)十一月二十六日,张之洞呈报清廷《筹设炼铁厂折》曰:“内地铁货出洋。以锅为大宗。其往新嘉坡。新旧金山等处。由佛山贩去者。约五十余万口。由汕头贩去者。约三十万口(惠州淡水贩去者。约二十万口)。由廉州运往越南者。约四万口。”此折无论是“汕头贩去者”,包括“惠州淡水”“约二十万口”,或者“惠州”单列,它都是明确的事实。当然,这“二十万口”铁锅仅为“出洋”商品,并未包括还存在的内销部分。铁锅生产需要一条完整的产业链,同时需视其规模大小,投入资金、技术、人数等大量生产资料。其中铁矿的就近采掘也是一项降低成本,提高利润的重要环节。《惠阳县志》“矿产资源”中,“铁矿”条目讲道:“沿县东半部分布。除天光铁矿为小型外,其余皆为矿点或矿化点,其中天光铁矿、秋长铁矿曾经有小规模露天开采。”必须说明的是,《惠阳县志》的陈述,大约是“洋务运动”百年之后。早在宋代的《元丰九域志》中就有惠州采矿的记载,惠州采矿业历史悠久且矿物储藏量丰富,以淡水铁锅年产二十万口规模的铁矿石用量,当地是可以满足供应的。
《朝东华录》载:光绪二十一年(1895),上谕:“中国制造机器等局不下八九处。历年耗费不赀。一旦用兵。仍须向外洋采购军火。”
这等于诏告了洋务运动的寿终正寢。梳理当年的做法,如招商局开办企业时拨给官款,并规定在一定年份内按股金不等数款收回。又如官督商办企业,虽然吸收私人股金,但完全由官方主持,认股的商人对企业的管理没有任何发言权,一切权力都由官方指派的总办、帮办等人掌握。这类官僚经营措施非但缰化,而且无效,它只能说明在形式上做了这件事情。
末完待续!
编辑:惠阳区南宝东江流域古陶瓷博物馆,张旋
2022年4月19日
-
2022-02-07
-
2022-02-14
-
2022-01-27
-
2022-02-21
-
2020-05-28
-
2022-04-19
-
2020-06-03
-
2022-03-23
-
2024-08-12
-
2020-05-28
热点资讯
